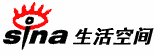 |
|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文化艺术 >光明日报 > 新闻报道 |
| |
胡 明 http://www.sina.com.cn 1999年8月27日 11:34 光明日报  《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一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培元、李明生就将样书送来给我,我是这本书最 早的读者之一。这本书酝酿之初,他们也郑重地邀请我写一篇。他们知道,我是我们这一辈中极少数几个有幸受到过钱先生亲 炙的人。当时我没有答应下来,我知道钱先生对“写他”和“研究他”--不管是动机还是效果总是疑心重重的,更由于一大 批钱先生生前知己好友都在动手写纪念回忆文字,我想我又何必也轧进去凑数。两天读完这一册35万字的书,心里不免生起 些激动,也浮起许多回忆,忍不住有些话想说。 钱先生已经逝世半年多了,算是我的一份迟到的纪念吧。 书名“钱钟书其人其文”,篇目大抵两类:纪念“其人”的和研究“其文”的,领衔作者是我们社科院的前辈学 者,亦有不少是我的师长、同事和朋友。文章分两类,作者其实很多是可以交叉打通的。如敏泽先生的文章无疑是“钱学”研 究的学术巨制,但他完全能写出更详实更丰赡的回忆文字;如傅璇琮先生的“缅怀”,当然以回忆为主,但他也完全可以做出 厚重精湛的“钱学”研究。又如我的同事刘士杰的“幸福的回忆”,学术味与人情味并重,读后如饮甘泉,有一种纯粹智慧的 餍足和亲切动人的历史感。通阅全书,钱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他的思想智慧、他的人格境界、他的个性魅力、他的澹泊高洁 、他的机敏深刻,仰视这一座远在天边的“文化昆仑”,毕竟真有“走近钱钟书”的感觉。所谓“高山仰止”,愈走近,广大 读者愈会感到云里雾里,仰之弥高。钱先生在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仍然是一尊高坐云端的文化之“神”。这本书试图传达出这 么一个信息:钱先生虽然是一尊文化巨神,但亦是一个温情脉脉的普通人--“昆仑”山景大抵如此。怀抱深远去往“昆仑” 山中学道学剑者大多无功而返,他们眼高性急,找不到“下手”处;游戏山下掇拾花草者往往收获甚丰,他们因“散淡”而得 真谛。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我很幸运,不但“走近”过钱先生,而且有机会、有条件与钱先生在极近的心理距 离上作过多次长谈,动辄几个小时,如坐春风,更幸运的是这种长谈又往往有杨季康先生一同参加。那一段时间正是钱先生夫 妇住在南沙沟6号楼深居简出的晚年。虽然深居简出,但他们对中国学术界与我们两个文学所的事却知道得很多。在我的印象 中,他们也很希望有信得过、谈得来的同事和朋友来聊聊天。我的拜访也是他们学术工作忙碌之余的一个调剂,看得出,他们 很欢迎。 我们聊天说上海话,钱先生的上海话多点无锡口音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辞,我的话题更多的是六七十年代的上海 新典故和文学所里80年代初的人物春秋。我们不谈学术问题,更不提典籍文献,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人物,人物当然不是陶谢 韩柳、李杜苏黄,而往往是何其芳、俞平伯、余冠英、吴世昌等,有时也谈钱钟联、程千帆;外文一摊的则是戈宝权、卞之琳 、罗大冈,也偶尔谈及冯至、穆旦;杨先生谈得更多的是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陆小曼、林徽因等。我的印象中钱先生谈 风气象阔大,机锋闪烁,语调如行云流水,但言辞犀利而雅洁,往往一目全牛,片语中的,也时时有李慎之先生说的那种“口 没遮拦”,处处显出先生性情开朗、襟怀豁露,处处显出先生学术人品的高风亮节。风之“高”:俯视宇内,超越一代;节之 “亮”:清光照彻,一片纯明。与钱先生谈话,获益最多的倒不是那些学术人物的评价,而是感染到洞烛世事、辨识人心的一 种敏悟和行止方圆、大节进退的一种自觉,这种感染最滋润我的灵魂,给我的“欣悦”是无尽的。 与钱先生的交往中有三件事,印象很深。第一件事与江绍原有关。钱先生曾给《文学评论丛刊》推荐来一篇江绍 原的论楚辞的文章,我接到稿子一看,很感兴趣。谁知道,这一期的《丛刊》还没有印出来,我却接到了江绍原逝世的通知。 通知要我某日下午一时半到商务印书馆集合,统一坐车去东郊火葬场与遗体告别。遗体告别那天,人去了不少,我刚走进那个 简陋又拥挤的等候厅,就听到有人在呼叫我的名字:“胡明,胡明,到这边来!”我抬眼望去,在等候厅的一个隅角里,一张 破旧的乒乓台边的长条凳上坐着杨季康先生,钱钟书先生站在那里不停向我招手。人群一堆一堆在聊天等候,居然没有一个人 认识、更没有一个人照应钱先生夫妇,他俩孤单地?缩在那个隅角里。我赶紧挤过去与他们握手,钱先生脸上露出的喜悦近乎 天真,激动地说:“你也来了,太好了!”于是我们坐下来边说话边等候。原先安排在下午第一场的告别仪式因故改为第二场 --我们在东郊火葬场那个等候厅的隅角的长条凳上几乎谈了3个小时!那次的谈话内容(话题十分宽阔,也破例谈了许多学 术,他还委托我传话给许觉民所长,下达好几条指示--钱先生是副院长作者注)至今清晰可忆,但是那天钱先生头里的委屈 和后来的兴致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神”,有时也怕寂寞、也怕孤单,也怕意料不到的“冷落”。钱先生招呼我时的 那份天真与激动,我终身难忘。 第二件事是有关胡适的。一次我拜访钱先生时顺便提及台湾刚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一节胡适称美 钱先生的谈话。我复述给他听:一位香港的朋友给胡适带来一本钱先生的《宋诗选注》。胡适便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钱钟 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回答,10年前在南京匆匆见过一面,并说你是钱基博先生的 儿子,英文很好。胡适马上说:岂止英文好,中文也好。钱先生听着笑了,过了一会儿说:胡适之是“贵人多忘事”,他是见 过我的,也是在南京,一次文学圈子里的什么聚会。胡适之正好也在南京,当然就被请来当贵宾,坐在首席。我记得当时我还 走到胡适坐的桌子边,向他请教几个问题。胡适之答话没说完,便被什么人叫过去了。那时我还年轻,他则是大名人,大权威 ,“所以,我钱钟书认得他胡适之,他胡适之不认得我钱钟书”。--末两句话加了引号,正是由于我印象特别深刻。钱钟书 年轻时也有这一番见名人的经历,也有过一番面对名人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的心结。胡适对钱钟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 ,他称赏《宋诗选注》“确实写得不错”。 第三件事是钱先生曾对我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那是发表在1988年第3期《文学遗产》上的《古典文学研究 的现实危机与暂行出路》。文章刚出校样时,所里围绕我的这篇文章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有的说“很好”,有的说“很不好 ”。钱先生在家里不知怎么也很快读了这篇文章,他明确表示欣赏,并传话给当时所里的主要领导:我好多年没有读到过这样 痛快淋漓的文章了,请转达给胡明同志我的这个意见。他还私下对老朋友说:胡明这小鬼,孺子可教。90年代初,我去看望 他时,他仍是指着我说:“你是孺子可教,一点就通。”又笑问:“听说最近又闯祸了?”当时我给他送去我的一本新出的书 《南宋诗人论》,他翻了几翻就放下了,他的“孺子可教”显然不在学术学问上。我看得出,大抵他欣赏的是一种人文态度、 一种人文风格,或者说是一种学术姿态,当然钱先生也很留意文章的技术。就是论学术,他也是更讲求一种宏观的识度与悟性 ,一种骑在历史肩上的姿态。前面我说的“很近的心理距离”大致也是指这一个观察与对话的角度。 钱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义独特的文化巨人,或者说姿态独特的“文化昆仑”,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文化时代的 终结,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绝学”。翻过中国学术史的这一页,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钱钟书的出现,更不会有丁伟志先生期 盼的“钱钟书式的学者群的涌现”。得以产生钱钟书的时代条件不存在了,钱钟书的“块然孤喟”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 多数学人能理解与觉悟的。他与我们太“隔”了,他与我们这个世界号称主流的文化学术圈的人和事太“隔”了。文化上他有 强烈的“叛逆”倾向,时时有跟伪文明捣蛋的意图。也正是因为他的天才与操守,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完美自足的一个特例。 巍巍”昆仑”,悠悠“文化”,钱钟书已经走进了历史,我们自己又如何来对待现实的残缺呢?  与来访者高谈阔论是钱先生的一种休息方式? |
|||
|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文化艺术 >光明日报 > 新闻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