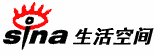 |
|
|
|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旅游 >新疆银宇 > 新闻报道 |
| |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3月30日 15:36 新疆银宇 本文作者周辉。 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我国的 敦煌和吐鲁番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在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交汇点。(季羡林) 从吐鲁番到敦煌——记大海道考古探险穿越 全长500多公里的大海道,是已知的十四条丝绸之路中最后一条未被探明的故道,在它的两端,连接着丝绸之路上 两个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重镇——吐鲁番和敦煌。 大海道一名的由来,史书上没有正式记载,大概是因为这一路上多沙碛荒漠而得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 家孟凡人介绍,大海道是14条丝绸之路中最不为人熟悉的一条,也是其中最为危险的一条。由于它是中央政府通往西域最近 的路线,比旁边绿洲遍布的哈密路线缩短了近一半路程,因此,自汉唐到宋元时期,在军事、经济上的位置都极为重要。元代 以后,由于沙漠化加剧,废弃不用。明清以来,中外各国的考古队曾做过几次穿越的努力,但都以失败告终。 2000年2月1日到1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举行了大海道考古探险穿越活动,在12天 的时间里,14名队员乘坐着沙漠车爬涉漫长的无人区,沿途经过了废弃的古城堡、烽燧、驿站、史前人类居住遗址、化石山 ,遭遇海市蜃楼、沙漠野骆驼群、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这是一段辛苦、却精彩纷呈的行程。回来好些天以后,想起那些 恍如洪荒年代的景与物,仍然有一些不太真实的感觉,好象我们一路经过的,并不是人间的风景。 起点——富庶丰饶之地 吐鲁番,突厥语的意思是富庶丰饶的地方,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哪个城市象吐鲁番这样富于传奇 色彩。西出玉门关,库鲁克塔格以北、火焰山南麓,戈壁、流沙、干涸的古河道包围着的这片绿洲,就是吐鲁番。在它的北方 ,天山山脉终年积雪,静静矗立。 吐鲁番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交叉点上,这种重要的战略位置为东方、西方和北方游牧文化的 汇聚创造了条件。“如果说西域文化是一种十字路口文化的话,那么这一特点在吐鲁番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引自中国社 科院历史所余太山主编的《西域文化史》)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无论是南道还是北道,都必须穿越中亚广阔的戈壁荒漠地 带。一到夏天,骆驼开始换毛,体力衰弱、不堪使用。而在酷热并且最易起暴风的夏季到没有一滴水的沙漠中旅行,也是完全 不可能的。因此东西往来的商贾、僧侣、使者常常选择风最少的冬季开始他们在中亚地区艰难的旅程。吐鲁番冬季平均温度比 周围其他地区高出差不多十度,无疑是行旅们向往的乐土。 今天,在吐鲁番依然屹立着当年丝绸之路上两座西域最大的古城——交河城和高昌城,这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5处,占了全新疆的50%,在自治区历史博物馆里收藏的西汉到唐朝、也就是丝绸之路昌盛的一千多年间的文物,80% 以上出自吐鲁番。丰富的文物和遗迹,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中亚史、东西方交流史、以及西域史的最佳佐证,同时也为我们勾勒 出这片绿洲当年的繁华。 汉唐盛世之间的一千多年里,吐鲁番以开放的姿态迎纳了东西方几乎所有最伟大的古代文明。在长安、波斯、君士旦 丁堡,当一种文明或宗教受排挤不得不远走他乡时,他们也常常会选择吐鲁番,穿过河西走廊或翻越帕米尔高原,在吐鲁番找 到适宜的土壤。 关于佛教:20世纪初为追蹑佛教东渐史迹几赴新疆的东瀛释子橘瑞超曾经在他的中亚探险记里写道,吐鲁番是佛教 东渐史上最重要的地方。在高昌城和交河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大量汉唐之间的佛寺遗址。吐鲁番的佛教石窟寺群多达十余处 ,合称高昌石窟,它与新疆的龟兹石窟,以敦煌、云岗石窟为代表的中原石窟,以及印度最大和石窟遗址——阿旃陀石窟齐名 ,是世界佛教石窟艺术的四大代表之一。 摩尼教:吐鲁番曾经是摩尼教的世界中心,在吐鲁番发现了这个宗教最初的文献原稿,而吐鲁番的摩尼教绘画,是这 个已经灭亡了的世界性宗教艺术上至今尚存的唯一见证。“没有任何东西,能比吐鲁番保存下来的细密画更清楚地向我们展现 摩尼教的精神世界。” 只要有心,在吐鲁番可以找到各种古代的宗教遗存,比如梵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的佛经写本,萨满教图腾,一千多 年前的基督教堂遗址,以及反映道家思想的壁画等。实际上,这个今天以葡萄园艺和维吾尔民间风情闻名的戈壁绿洲,曾经是 世界上古代宗教最活跃最发达的地方。我们的大海道之行,是带着震惊和欣喜开始的——在这里,文明曾经如花般绽放。 史前居住遗址 穿过鲁克沁镇再往东南,我们经过的这片石器遗址,就在离公路不远的地方。它的北面,是库姆塔格沙漠。南面,是 觉罗塔格山。在维吾尔语中,库姆塔格的意思是沙山,而觉罗塔格,是荒凉的山。我们经过的石器遗址、这片史前人类的栖息 地,就在沙与荒凉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一下车,中央电视台两个年轻的记者就连连感叹,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住人?在眼睛看 得见的地方,没有树。因为是冬天,我们也找不见任何绿色。只有几间维吾尔人土坯垒的房子,零零星星坐落在路边,映着冬 季灰白的天空,寂寞无比。 社科院的李肖博士感慨说,新疆的山,本来就大多寸草不生,够荒凉的了,而这条山脉,还被称作觉罗塔格,是荒凉 之中的荒凉。但是,他话锋一转:在几千年前、一万年前,也许这里水草丰美,非常地适合人类居住。 在更久远的时候,古地中海一址延伸到了新疆,今天的喀什地区,当年就处于地中海之中,相距一千多公里的吐鲁番 ,受古地中海的影响,气候湿润、林木繁盛。我们看到的石器遗址,实际上是在一条干涸的古河流的河岸上。 经过几千年风剥日蚀,当年人们生活的痕迹大多荡然不存,曾经覆盖在遗址上的松散材料早已被风吹离,只有那些石 制品和各种未经加工的石头留了下来。在由沙构成的几个高地上,石制品几乎随处可见,在阳光底下,显示出和周围地表不一 样的光泽。我们拾了几片,有石核、橄榄形石片制成的刮削器等。小石片的形状很不规则,厚薄、长短不一,侧面有明显的经 过人工打凿的痕迹。制作材料包括灰色、绿色燧石,玛瑙,石英石等。在一枚般底形石核上,还保存着完整的菊叶虫化石。 手里握着几片一万年前的人们使用过的石器,站在他们的脚可能也踩过的地方,心里的感觉非常神奇,一万年前的人 们好象倏忽而至,近得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吸,就在你的耳边,缓缓地讲他们是怎样生活和思想的、他们的居所和社会。 几年前,读到一本考古学的小册子,这样讲述考古:无疑你可能必需去搬运与筛滤许多泥土,记住某些烦人的日期, 难为你的舌头去学说毫无意义的方言土语,并且试图去掌握那犹如相扑摔跤手一样彼此冲突的理论。但与此同时,你也将被带 入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有着艺术与器物、庙宇与工具、陵墓与宝藏、失踪的城市与神秘的手稿,木乃伊与猛犸象…… “考古学”如同一个平静的大海,浩翰、深沉,水面上反射着迷人的阳光。看见李博士低着头从一个高地踱到另一个 高地,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由不得人不心生羡慕。我们在琐碎的生活里奔忙,在如昙花一现的功名利禄里陶醉,不是每 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常常面对自己的心灵,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快乐,并且回答说,是。 通常史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物是陶器,因为停留时间短,我们仅简单地走了走,没有发现陶器。拾得的几片石器,在 离开时都放在了原地。 夜宿觉罗塔格山间谷地,晚上变了风向,清早起来,发现我们扎营的地方正好在风口上。帐篷内凌晨的温度是摄氏零 下18度,人人帽子上顶着一头白霜爬起来。在外衣上溅落几滴水,马上冻成了小冰疙瘩,真正领会到滴水成冰、哈气成霜。 因为风大,水烧了两个小时仍然不开,各自啃了些干粮。 这是第一天。 最后的村庄 迪坎儿是鄯善县最南端的一个乡。从迪坎儿往南,可以进入罗布泊,通楼兰城。在古代,这条路线是通往楼兰的几条 主要路线之一。因为从迪坎儿往南,就进入罗布荒漠地带,从此人烟罕见,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作“最后的村庄”,或是“零 的村庄”。我们走大海道,一直往东南行,迪坎儿同样是最后的驿站。 中午在路边的一家小店休息,很偶然地听说迪坎儿南面有座化石山,满山都是化石,大家决定去看一看。 迪坎儿的乡民淳朴而热情,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几个向导:伊不拉提、伊不拉提的儿子和朋友,都是维吾尔人。据说这 座化石山,最早就是这两个年轻的孩子发现的。伊不拉提和我们一起挤坐在驾驶室里,两个孩子三两下就跃进了后面的拖车。 我们不懂维语,两个孩子又不懂汉语,遇到要转方向的地方,两个孩子就拍着车板在后面大声喊,伊不拉提再翻译给 我们。穿过一片戈壁,进山,再翻过几道山梁,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化石山。早就听说有经验的维吾尔猎人即使蒙上眼 睛也不会在沙漠或是崇山峻岭间迷失方向,但是两个年轻的孩子在看不到任何明显标志物的情况下,在层层叠叠的山峦之间, 将我们准确地带到了目的地,仍然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有些惊讶。 我们眼前的这座化石山并不太高,相对高度在100—200米之间,地表就是裸露的化石层,随手拾起一块巴掌大 的石头,表面能看见好几枚贝壳,非常完整。往山上爬的时候,几乎每走一步都会踩上化石,走得人心惊肉跳。两个维吾尔孩 子说,他们曾经在这里拾到过一条完整的石头鱼,听他们描述,可能就是50年代初古生物学者在吐鲁番发现的吐鲁番鳕鱼化 石。这种鳕鱼生活在两亿年前,头部尖锐、身体如梭,混身披覆着斜方格状的鱼鳞,通过它们的生活环境,古生物学者推断出 当年吐鲁番曾经是一片面积广阔的淡水湖泊。 几十年来,在桃树园子、柯柯亚、胜金口、苏巴石、连木沁、红山、七克台、飞跃、大步、十三间房等许多地方,古 生物学者不断发现庞大的古生物群落——吐鲁番鳕鱼、吐鲁番兽、吐鲁番鳄鱼、吐鲁番巨犀、水龙兽、袁氏加斯马吐龙、武氏 鳄、恐角兽等,大量的化石资料引领着我们的目光掠过吐鲁番盆地无边的戈壁和荒漠,进入一个古生物的乐园。而我们经过的 这座化石山,这些凝固的生命,在几亿年来,在吐鲁番大地上生活过的所有生命之中,如沧海一粟。 晚上投宿在一家采矿点上,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小地方。虽然标牌上写明这是一家花岗岩矿,工人却告诉我们,这里 其实是金矿。矿点上唯一的建筑是一排低矮的砖房,屋外墙壁上写着两首长长的爱情诗,格调忧伤,据说出自老板之手。晚上 ,矿点上唯一的一个小媳妇一面帮我们做饭,一面和我们唠家常,在昏暗的炉火边,在寸草不生的山与山之间清冷的小屋里, 听她讲自己的孩子,讲自己在这么荒凉的地方打工,希望可以供得起孩子在家乡读书,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几天以后,路遇一些找矿的人,听他们描述,我们投宿的这个矿点有过不少令人发指的恶行。零零星星的话,让一个 看似简单的小矿点顿时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想一想,采矿人的生活里应该有不少波澜起伏的故事吧,只是在惊鸿一瞥般的行程 里,我们无缘深入。这是第二天。 进入无人区 离开路线中的最后一个矿点后,我们进入无人区,连着几天的时间里,我们的车一直在没有路、几乎看不见任何人类 生存痕迹的戈壁、山地、甚至是古河道中颠簸前行。每天早上从给养车里取出定量的水、馕和水果,按人头分配到各个车里, 饿了掰块馕、渴了喝口水,直到黄昏时的下一个宿营地。 车一直往东南行,每天太阳从左边的车窗升起,在右边的车窗落下,惹得靠右车窗坐着的骆老师笑说,到了目的地我 的右脸一定比左脸黑。 虽然是无人区,行程却并不单调乏味。 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常常是刚刚觉得一种地理地貌有些冗长时,峰回路转 ,又是另一番天地,比如:绵延几十公里的金红色的砂山、盐壳覆盖着的巨大的古代湖盆、被风沙打磨得千姿百态的山石、以 及宽阔得比长江黄河毫不逊色的古河床,大气天成、在不一样的阳光底下,流露出让人震惊的美丽。 一路上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一个地质学者同行。在地质学者的世界里,山与地与每一块石头都是有生命的,而我们这 次却无缘解读了。 晚上一直宿野外,北京搜狐公司的小于常常拉了李博士要求讲故事,然后一个个记下来发回公司,成为搜狐网站大海 道探险网页的主要内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每天工作到半夜两三点钟,负责传送新闻的同志则有时整夜不能休息。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星光清澈得好象近在咫尺,而我们,象是在星光之间游走。 这是第三天到第五天。 看见野骆驼 这是一个牧人讲述的故事:上帝派了一个神到地上来变作回教僧徒,叫他到教长亚伯拉罕那里去要一群他养的家畜。 亚伯拉罕很慷慨地允许了那回教僧徒的要求,所以他自己反穷了。然后上帝又叫那回教僧徒将所有的牲口还给亚伯拉罕,但亚 伯拉罕不愿将他已经给了人的东西拿回去。上帝发起怒来,命令那些牲口从此在世界上无所依归的漫游,它们就变成了野绵羊 、山羊、野牦牛、野马和野骆驼。 差不多一百年前,喀什葛尔的牧人向斯文泛斩ń彩隽苏飧龉适 ”皇赵谒穆眯屑抢� 。 同样是一百多年前,一个俄国人带了一张野骆驼皮回到自己圣彼得堡的家中,后来他对斯文-赫定说,这类奇兽只有 我们现在所在地方极东方的罗布淖尔沙漠才有。 因为我们的路线正好经过罗布沙漠北缘,大家都存了一些奢侈的想法,希望可以见到这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虽然据 说它们今天在全世界已经只有不到三百只。 出发前一天,摄像记者驾驶空气动力伞进行航拍,在离一个村子几十里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骆驼,拍摄回来准备作为野 骆驼上新闻,被专家制止了。野骆驼喜欢三五成群的活动,在总量已经不到三百只的情况下,在离村子这么近的地方,一次看 见几十只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次经历让大家都有些扫兴,上路以后,“前方发现野骆驼”成了队员们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以至于最后终于发现了 野骆驼时,前几声吆喝就有一些“狼来了”的嫌疑,没人理睬。 这一天上路以后的所有经历,都好象是在为发现野骆驼做铺垫。 先是经过了一处面积很大的草滩,大概是季节河的流经之处,盐碱翻上来,白花花地耀人眼。在朝阳面的沙包前,我 们看见大量新鲜的骆驼粪,还有骆驼坐卧过的痕迹。 再往前走,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我们进入踏上大海道以来最长的植被带。走了一半,巫博士突然大喊停车。这是麻黄 草啊,提练出冰毒以后,价格比黄金还贵,巫博士有些激动,记者赶紧紧张地拍摄,其他人也三三两两下了车,在麻黄草丛之 间活动活动腿脚。一个拿着望远镜东张西望的小伙子突然大喊一声:前面是什么?引得大家都往前面的山梁上望,一阵沉默后 ,终于有人叫出来:骆驼!四只骆驼。十几个人手忙脚乱往就近的车上跳,一阵风驰电掣赶过去,正好看见几只野骆驼悠悠闲 闲、混然不是逃跑的样子翻过山梁不见了。 这天最后一次看见野骆驼是在一条山谷里,两只、母子俩,听到车的轰鸣声,开始撒足狂奔,两只驼起先是一前一后 沿着山谷跑,眼看就要被我们的车赶上的时候,母驼将幼驼轻轻往山那边撞了撞,幼驼转身便跑进山里去了,母驼仍然沿着山 谷奔跑。开车的师傅忽然心疼地说,它是自己不要命了,救自己的娃娃。这句话触动了大家,几辆车陆续停了下来,一直恋恋 不舍的追逐着野驼身影的摄像机也停止了工作。 看着野驼妈妈缓缓地跑远,夕阳底下笼着金光的驼峰渐渐隐入沙漠植物背后,忽然有一种深深的抱歉和愧疚:它们是 这片荒漠的主人,我们都是不速之客,即使最后停止了追逐,我们仍然是它们平静生活的闯入者。我不知道,这场长达十余分 钟、50迈的赛跑,有没有伤了野驼妈妈的身体,那只被赶进山中的幼驼,已经和母亲相隔了六、七公里,它们可以重逢吗? 我们无心的错失,会不会让它从此失去了母亲的庇护?而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这是第六天。 厖 终点——春风不度玉门关 经过十来天跋涉,最后一天的行程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些迫不及待,第一次在日出之前每个人都收拾好了行囊,整装 待发了。 进入甘肃境内后,慢慢靠近人烟,风景也慢慢开始变得平淡,只有两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次是开车下一个近70度 的陡坡,一次是沙漠车误入疏勒河河床中心,险些陷在里面。 著名的疏勒河已经干涸了,河床中零星地点缀着几株沙生植物,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没人会注意到这里就是几十年前 的记载中还曾经波涛汹涌疏勒河。 翻上疏勒河岸,远远地可以看见小方盘古城,有学者认为,它就是汉时的玉门关。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的 玉门关。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就是经过的这个玉门关,讨伐匈奴的大军也曾经通过这个关门。从小方盘古城沿疏勒河 蜿蜒向西的汉长城依稀还能让我们体会到当年紧张的战争气氛,而如今,城、墙,连同绵延的烽火台,都已荒废了。 车轮辗过沙碛,缓缓驶向小方盘城,我们的行程渐近尾声。望着远处向我们挥手的身影,想起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 的一段话: 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之间 再次感谢吐鲁番地区、《丝路游》杂志对银宇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我游新 疆”栏目的大力支持! 相关专题:游新疆
|
|||
| 新浪首页 >生活空间 >旅游 >新疆银宇 > 新闻报道 | ||||
网站简介 | 网站导航 | 广告服务 | 中文阅读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帮助信息
Copyright (C) 2000 SINA.com, Stone Rich S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四通利方 新浪网